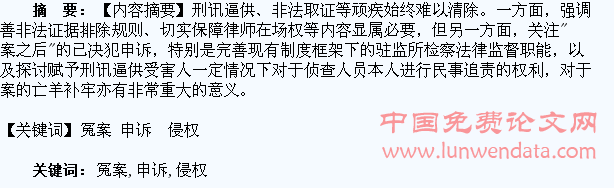
10年后,张高平站在再审法庭上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可能不是法官、检察官,假如没法律和规范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大概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这段话近期被各大媒体反复引用,成为了“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标志性话语。显然,这是张高平ro年无妄之灾的切肤之痛。“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有着“不变与变”。“不变”是说,刑讯逼供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典颁布30余年后的今天,依旧是制造冤案的最大主因;而“变”则言,相较于佘祥林案等“死者”复现才使沉冤昭雪的“由外而内”纠正错案的路径不同,张氏叔侄案中,驻监所检察官饰演了相当积极正面的角色。这应该成为促进大家认真察看、逐步深思现有监所检察规范的新契机。同时,与现有很多探讨诸如怎么样杜绝刑讯逼供,从规范侦查行为到健全审判程序等文献不同,本文立意于讨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背景下的“中国式冤案”发生后的救济问题:一方面,为防止“无效申诉”,应当加大对于已生效判决的监所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其次,对于推行了刑讯逼供,但因程度等缘由而没追究其刑事责任者,可借鉴比较法案例,赋予受害人对于侦查职员本人进行民事追责的权利。
1、防止“无效申诉”:加大驻监所检察对于已决犯申诉的法律监督职能。
实行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道环节,总是不让人看重,其实它更关乎刑事被追诉方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所以打造健全官方为主导的、各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的刑事申诉机制是每个法治昌明国家的一同选择。
这一点在中国更具现实意义。以张氏叔侄案涉及的死刑实行为例,因为在中国死刑案件判决宣布到复核程序结束大多只有2一3个月的时间,且案件一旦核准,依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实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以内出货实行”,这就愈加缩短了可能被冤枉的刑事被追诉方提起有效申诉的时间(甚或可以觉得这是一种对于正当权利的变相剥夺)。这方面的教训其实是惨痛的。①就此,笔者觉得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作为对已决犯申诉权利的保障,加大驻监所检察对于生效判决案件的法律监督职能无疑是一条可取的道路。
还以“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为例。就像窦娥见到了亲爹,苏三遇到了情郎,《十五贯》里况钟的出现,张氏叔侄不幸中的万幸就是遇到了新疆石河子人民检察院驻监所检察官张彪。
先看一段容易被忽略的采访。从2009年开始,张彪检察官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重新做了整理,连同所有些谈话笔录,一同寄给了浙江的有关部门,可“一直寄,一直没回话”。有记者问道:“根据常规,或者说根据规矩,他们应该回话么?”答:“应该回话。”问:“假如他们不回话,大家做不了任何别的努力么?”答:“那还是继续再寄吧。”问:“如此反反复复寄了多少次?”答:“有5、6次吧。”问:“都没回话?”答:“都没回话。”问:“除去寄就没别的任何办法?”
(长长叹气后)答:“等待。”②“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中,驻监所检察有哪些用途至关要紧,值得重点关注。正是因为监所检察的存在,使得这起冤案很罕见地“由内而外”地打开了司法救济的大门。这类年很多震撼全国的冤案中,佘祥林有“复活”的老婆,杜培武等来了杀妻真凶,被赵作海“谋杀”的同姓赵振晌时隔10年回村,上述“中国式冤案”的一同特征,除开“人死复活”即是“真凶出现”,而张氏叔侄案中,出现了一个张彪,可以说,他所作的所有,相当程度地诊释了检察官本应负有些客观义务。
张高平的申诉行为显然可以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找到依据。该法第241条赋予了已决犯有关申诉权利:“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不可以停止判决、裁定的实行。”可问题是,提出该申诉后的效力怎么样,法律并没明确,这种宣喻性条文在实践中非常难被有关部门理会,申诉成为“无效申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事实上,张氏叔侄一案中,其代理律师朱明勇“接手这个案子,首次去了浙江高级人民法院时就发现,张氏叔侄本人和家人之前7年的申诉,从未被登记过。”③在这种司法实践的状况下,更应将讨论重点放在驻监所检察官张彪3年以来“5、6次”将采集到质疑原审判决的材料寄送到浙江有关部门的行为,即监所检察官对于已决犯判决的法律监督行为上。仔细研读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64条规定:“监狱和其他实行机关在刑罚实行中,假如觉得判决有错误或者罪犯提出申诉,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处置”,可以看到,即便在本次刑诉法修正案大大扩充了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状况下,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的同意罪犯提出申诉的部门也是监狱而非检察院。而在本案中,尽到审慎处置罪犯申诉、客观剖析案情、最后帮助无辜者洗冤的并不是监狱方面而是驻监所检察官。更值得玩味的是,据张高平在采访中回忆,“张警官”(张高平语)承受了来自体制内的“非常大的重压”。④张彪检察官口称的“等待”与承受的“非常大的重压”无疑反映了检所检察规范对于已决犯判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尴尬近况。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对于《宪法》
第129条规定的“中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落实。
上文已提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于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之前法典中的很多原则性规定得以细化、落实。⑤其中,有关直接或间接涉及监所检察监督的内容达40余条,涵盖证据规范、强制手段、审判程序、刑罚实行、特别程序等每个方面。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颁布的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中,亦明确了监所检察是人民检察院的要紧职能之一,⑦主要集中规定在第14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一章中。具体包含第6节“羁押和办案期限监督”、第7节“看守所执法活动监督”、第8节“刑事判决、裁定实行监督”,与第9节“强制医疗实行监督”等。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此次刑诉法修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内容非常大程度上体目前强化刑事实行法律监督方面,特别是在很多条文中均规定了刚性期限限制,但对于监所检察官发现已决判决的可能错误后怎么样处置与有关刚性约束期限的规定上,付之网如。这也就是上文中记者所提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除去寄就没别的任何办法?”
其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关于加大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中就已经明确了监所检察的主要职责,其中第4条第8项规定:“受理被监管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第16条规定:“对被监管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申诉,经审察觉得原判决有错误可能的,移送申诉检察部门办理,觉得申诉理由不成立的,做好息诉工作。”也就是说,监所检察对于已决判决可能错误的法律监督虽然没明确体目前刑事诉讼法典之中,但在有权讲解的规定中是明确的。之所以出现张彪检察官所碰到的瓶颈,显然还是由于法律监督的这一方面职能并没得到应有看重,司法讲解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却没任何细化可操作性条文。
另外,人力资源的相对匾乏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据调查,看守所根据14%的比率配置警力,监狱、劳教所根据18%的比率配置警力,而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看守所一般根据0.5%一1%的比率配置检察职员,派驻监狱、劳教所一般根据1%。的比率配置检察职员。⑧截至200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有监所派出检察院80个,派驻检察室3204个,这类派出、派驻检察机构共有派驻检察职员9(X)0多人,对全国95%的监管场合实行了派驻检察。⑨可以看到,每一个派驻检察室检察官数目不足3人。结合上述列明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于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充,特别是对于实行阶段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充,根据现在的人力物力配置,显然非常难达到立法者意图达到的成效。
问题的解决也需从立法条文与人力物力配备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增强立法条文可操作性。如前所述,现有法律规范中,驻监所检察对于已决犯判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清楚,司法讲解虽有一定量的补充,但也是原则性规定,没操作价值。在以后的立法中,至少应在司法讲解中明确,比如,驻监所检察官发出的有关已决判决可能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文书,原判决做出地检察院应于3个月之内进行正式回复;假如驻监所检察官依然觉得原判存在错误,经其派出检察院赞同,可以向原判决做出地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继续反映,该院应于1个月之内回复,等等。
其次,既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扩充了检察院法律监督,特别是实行阶段法律监督职能,就应当在职员配备上给予充分保障。具体到驻监所检察监督问题上,有实务部门论者提出,应改革现行对监管场合实行的单一的派驻或巡回的检察监督模式,变为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结合的模式,即“健全派驻检察,增设上级巡回,扩大外部监督”,即在坚持原有属地的基层或分、州、市检察院向监管场合实行派驻检察制不变的状况下,对现有派驻检察体制机制不顺等问题加以增设上级巡回检察环节,同时扩大外部监督的途径,加大法律监督和自己监督的结合,以保证监所检察权的正确行使。⑩加大检察官对于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介人,俨然成为一种趋势。以美国为例,面对层出不穷的死刑类冤案,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拓展了一项名为“宪法计划”(COnstitutio。Project)的研究,提出了改革死刑的18项建议。其中最后一大多数即集中探讨了“检察官角色” (RaleofPro网站优化ut()rS)问题。⑧“我今年就要退休了,张辉、张高平的案子我期望你不要舍弃,每到夜晚,我想起张高平向我哭诉被刑讯逼供冤判的情形,我都没办法人眠。”“张高平他们后面的路如何走,我有的惦念。”—这是张彪检察官发给张高平叔侄律师的两个短信,读来让人颇为动容。假如“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的确反映了时下部分中国司法生态,那样,切实加大监所检察官对于已决犯生效判决法律监督的职能,显然是完成刑事诉讼法典“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的现实且急迫之选。
2、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能否追究执法职员个人民事侵权责任?
这里提出的,是在冤狱赔偿、侦查职员刑讯逼供行为给公民个人合法权益导致损害的案件中,除去国家赔偿这一方面的内容,能否考虑给予受害人对侦查职员本人有限度的民事追责权利。“有限度”即指有刑讯逼供的紧急侵权行为发生且有关侦查职员并没同意刑罚处罚的状况:
第一要区别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错案追究责任—对此问题的不予区别,是致使实践中国家赔偿很难达成的极主要原因。国家对于刑事错案的赔偿责任,应为只须是事实上的错案,无沦办案职员本身有无过错,国家均应负赔偿责任。而刑事错案追究责任,是指办案职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首要条件下出现错案,既应产生国家赔偿责任,又应追究办案职员责任。
而这里所要探讨的是赋予害人对侦查职员本人民事追责权利的情形,仅指侦查职员“故意”而为的刑讯逼供行为。
2012年《国家赔偿法》第7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员工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导致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同时,第16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员工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成本。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职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一点上,国内台湾区域采相同立场,其《冤狱赔偿法》第22条规定:“赔偿经费由国库负担依第1条规定实行职务之公务职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法,致生冤狱赔偿事件时,政府对该公务职员有求偿权。”也就是说,国内及台湾区域均否认受害人本人对侦查职员刑讯逼供致使损害的民事追诉权利。
如此处置的考虑可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是什么原因:一方面,中国法律已经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即触犯此罪名的侦查职员需承担刑事责任。依据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读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员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以殴打、捆绑、违法用械具等恶劣方法逼取口供的;(2)以较长期冻、饿、晒、烤等方法逼取口供,紧急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3)刑讯逼供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4)刑讯逼供,情节紧急,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导致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5)刑讯逼供,导致错案的;(6)刑讯逼供3人次以上的;(7)放纵、授意、指使、强迫别人刑讯逼供,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8)其他刑讯逼提供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可以看到,可以触犯该罪名的,行为恶性已经达到相当紧急的程度。且在司法实践中,除非出现《刑法》第247条后半句规定的极端状况,“……致人伤残、死亡的,根据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不然参与刑讯职员非常难被追究责任。其实这一点,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声称自己遭到刑讯逼供的抗辩非常难被检察院、法院采纳就能判断出来—抗辩都不被认定,怎么样能进行下一步的责任追究?对于那些事实上施加了刑讯,但尚未导致伤残、死亡等紧急后果的逼供行为,比如张氏叔侄及李怀亮一类冤案的当事人,赋予其针对刑讯逼供施加好友员的民事追责权利是可行的。一则在弥补受害人物质、精神损害,二则震慑警察以后类似行为。
其次,赋予受害人追究侦查职员个人民事侵权责任的权利,自然会产生对警察倦怠执法的担心。笔者觉得,在中国现时国情下,需将该种追诉权限定为有刑讯逼供的紧急侵权行为发生且不当侦查职员并没同意刑罚处罚的状况。
事实上,即便是英美法范围,对于不当侦查行为的民事追责也是极其小心的。⑩比如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仅在2007年希尔(Hill)一案判决⑩中明确了这一怎么看:警察不当行为并没免于民事侵权诉讼之特权,在执法中应尽良善义务。当然,该义务不需要达到完美,但要达到合理标准。
在美国,一直以侵权民事诉讼的方法解决警察不当侦查行为的类似纠纷。有美国学者论述道:“美国联邦宪法依正当程序平等保护所有公民。第1983条(指《美国法典》第42编第1983条—作者注)是国会通过法案的一部分,该条约旨在于联邦法院提供给公民一条保护上述权利的道路径。假如你的宪法性权利被以国家权威之名的个人或组织侵有,你就能在联邦法院依第1983条去起诉该个人或组织。”⑩在这里,该作者还提到了1961年的门罗案。⑩在这个案件中,13名芝加哥警察非法闯人了门罗家里。之后,他们把门罗带回了警察局并告知门罗卷人了一块谋杀案。其间,不允许门罗打电话、接触律师之类。但最后,门罗并没被起诉并且获释。由此,门罗依第1983条起诉那些警察及芝加哥市政府。这个案件的要紧意义在于,不只为权益受损公民提供了救济方法,更要紧的是很大震慑了那些专横官员。
还需要提及的是举证责任的问题。假如真的赋予受害人在没紧急伤残等状况下的民事追偿权利,就需要立法规定此种情形的举证责任倒置,这种似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做到这类并不困难,仅需侦查机关提供完整、连续的讯问录像即可。
当然,赋予受害人一定量对公务员个人的民事责任追偿权利涉及侵权归责原则,损害赔偿的重复填补,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交叉的协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另行审慎研究,这里只不过提供一种比较法上的可能性。
即便在中国现有行政司法体制大概保持不变的状况下,亦可以在两方面考虑改进对此类冤案赔偿的方法。一是提升现有冤案国家赔偿之标准。中国2012年《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天赔偿金根据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薪资计算”,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3条或者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导致紧急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看到,申请国家赔偿的门槛本就相应较高,这样安抚性规定无疑非常难使受害人从物质损害到精神损害层面得到足额相应赔偿与弥补。⑩而在美国冤案赔偿实践中,受害人总是可以得到相当高额的赔偿金。《美国法典》第28编第2513条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即“受死刑错误量刑者可获得低于每年10万USD之赔偿,受其他错误量刑者则低于每年5万USD之赔偿”⑥。实践中,惩罚性的“天价赔偿”屡屡出现。⑩其二,加大对于国家公职职员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故意性不当行为的内部行政惩戒力度 (internalpscivline)。比如,在美国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紧辅助兴功能之一即为刺激提升警察的职业水准。⑩而通过内部行政惩戒,则可以有效地向目的人群(targetpopulation)传达需要遵守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之理念及如若违反后的相应制裁办法。⑧。
3、结语。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⑧白岩松询问张高平以后的日子如何过,张高平明显一愣,说还没想好。白岩松只得接话说,“好好过”。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至亲故去了,妻离子散了,张氏叔侄们的机陛生活,路向何方?但愿他们对于以后的路,只不过暂时没想好,而不是想不好。









































